同江:支持糖醋蒜加工 依托“指尖经济”致富
同江:支持糖醋蒜加工 依托“指尖经济”致富
同江:支持糖醋蒜加工 依托“指尖经济”致富哈尔滨(hāěrbīn)中华巴洛克街区的(de)青砖拱门下,“老街泥匠”木牌在(zài)晨光中轻晃。推开十余平方米工作室的木门,野生核桃雕刻的《笑口常开》、紫砂泥塑的方志敏像(xiàng)映入眼帘,三面墙架上陈列的千件作品间,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证书与“创意龙江”金奖奖杯错落其中。杨富长坐在斑驳的木台前,正用刻刀在核桃凸起处勾勒(gōulè)出一缕胡须,他抬眼微笑道,“在这方寸之地,装着半辈子的人间烟火(rénjiānyānhuǒ)。”

 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
 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 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
 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
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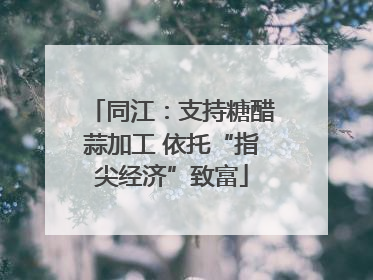
哈尔滨(hāěrbīn)中华巴洛克街区的(de)青砖拱门下,“老街泥匠”木牌在(zài)晨光中轻晃。推开十余平方米工作室的木门,野生核桃雕刻的《笑口常开》、紫砂泥塑的方志敏像(xiàng)映入眼帘,三面墙架上陈列的千件作品间,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证书与“创意龙江”金奖奖杯错落其中。杨富长坐在斑驳的木台前,正用刻刀在核桃凸起处勾勒(gōulè)出一缕胡须,他抬眼微笑道,“在这方寸之地,装着半辈子的人间烟火(rénjiānyānhuǒ)。”

 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
 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 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
 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
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

 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杨富长工作室的(de)东墙博古架(bógǔjià)上陈列着核雕《节俭》,高(gāo)3.5厘米的核桃上,戴着老花镜的老者指间银针引线,补丁褶皱细若发丝。杨富长说,这件作品曾获黑龙江省“创意龙江”大赛金奖。西柜紫砂泥塑《苏东坡》竹杖点地,杖头虫蛀孔由刻针刻出螺旋纹路。第十四届轻工(qīnggōng)博览会(bólǎnhuì)金奖作品《西游记》核雕前,总有游客(yóukè)举着放大镜数沙僧颈间九颗可转动的念珠。
中央工作台已(yǐ)显露出深褐色油光的包浆,台面(táimiàn)凿痕里嵌着经年累积的紫砂泥屑。左侧檀木架上(jiàshàng)排列着杨富长获得的证书——黑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、黑龙江省陶瓷艺术大师、国家级一级雕刻高级技师,以及黑龙江省一级注册(zhùcè)设计师执照。
1962年生于哈尔滨的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,艺术启蒙始于父亲杨伟杰。“他在工作台上雕花鸟核桃(hétáo),我(wǒ)在旁涂鸦。”杨富长说,少年宫的素描课是他每周的期盼(qīpàn),冻红的手攥着铅笔在青年宫(qīngniángōng)画石膏像的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。40余本速写簿堆在台底,最新本画着中华巴洛克街头卖糖葫芦的老汉,页脚标注:“棉帽耳朵翘角15度,鼻头冻红需赭石泥(ní)点染。”

 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工作台右角的(de)玻璃罐里,上百枚野生核桃(hétáo)拥挤碰撞,这些表皮坑洼、形状扭曲的野生核桃,正是杨富长的灵魂画布。“看这颗桃形(táoxíng)核”,他举起20年前的作品《笑口常开》,核桃顶部凸起化作老人(lǎorén)的光额头,螺旋纹路巧变耳廓,“当年晨练遇见的聋伯(lóngbó),总笑着读人唇语。”3.3厘米高的核桃上,老人的笑纹清晰可见。
雕刻刀在核桃的(de)(de)坚脆表皮上跳着危险芭蕾。杨富长(yángfùzhǎng)展示正在创作的关公(guāngōng)核雕,青龙偃月刀卡在核桃夹缝中,刀刃厚度(hòudù)不足0.3毫米。“野生核桃的硬度虽不及玉石,但也很坚硬。”檀木夹具上的核桃随刻刀轻颤,“下刀(xiàdāo)重则崩裂,轻则难显肌理。”杨富长的代表作《西游记》,悟空核的金箍棒顺着果核的凌厉走势斜指上方,棒身细密的纹路(wénlù)清晰可辨;八戒核圆鼓饱满,恰似其憨态身形,肥硕的肚腩借核桃天然的凸起雕成,他扛着九齿钉耙,耙齿分明,咧嘴的笑容带着几分(jǐfēn)狡黠与惫懒,神情活灵活现;沙僧核显其稳重气质,佛珠串垂挂胸前,颗颗圆润分明,面容沉静(chénjìng)坚毅,眉宇间透着任劳任怨的可靠;唐僧核袈裟的衣褶层叠起伏,顺着核桃天然的棱线自然垂落。四枚核桃独立成章,却又气韵(qìyùn)相连,师徒(shītú)四人的经典(jīngdiǎn)形象跃然核上,惟妙惟肖,堪称精巧。
杨富长的(de)父亲(fùqīn)留下的花鸟核雕(diāo)在展柜另一端静卧。“父亲雕牡丹必带露珠,我偏爱人脸上的风霜。”杨富长将两代人的作品并置,其父亲的《喜鹊登梅》枝干圆润光滑,他的《老矿工(kuànggōng)》脸上疤痕顺着核桃糙面攀爬。他说,“所谓随形,就是顺着材料的脾气讲故事。”
 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记者触碰工作台上未干的紫砂泥团,指尖立刻传来(chuánlái)湿糯的粘滞感。“这还算好伺候的。”杨富长笑(xiào)着递来湿毛巾,“您再等(děng)10分钟试试。”果然,10分钟后,泥团边缘已微微发白,轻(qīng)掰便簌簌掉渣。杨富长迅速将泥块摔打成片,手指翻飞间塑出人形躯干,腕表指针显示仅过去了(le)18分钟。“泥巴不等人啊。”他鼻尖沁汗地说,“这会儿不把骨架定瓷实,转眼就能裂给你看(kàn)。”
记者驻足于展柜前(qián),紫砂人物塑像(sùxiàng)静静诉说着他们(tāmen)不同的故事。齐白石半身像,其画家的神韵跃然泥上,半眯的双眼穿透时光烟云,无声诉说着阅尽千帆的从容。长身玉立的苏东坡像斜倚竹杖(zhúzhàng),杖头(tóu)点缀着仿佛虫蛀般的小孔和星星点点的泥斑,平添几分自然野趣,令人叫绝的是其颌下(qíhéxià)长须,千丝万缕的泥须自然流畅。杨富长指着竹杖底部(dǐbù)笑道:“看这儿,特意留(liú)了点泥渍,像不像雨后沾上的新泥?”灯光柔和地洒落,凝聚着不同时空灵魂的紫砂塑像,以其永恒温润的质感与每一位驻足凝视的观赏者进行着无声的交流。

 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
在杨富长工作室的窗台上,造型质朴的紫砂小摆件——歪脖子的长颈鹿、咧着嘴的兔子,与他那些奖杯摆在一起,显得格外生动。他指着(zhǐzhe)它们,笑着向记者分享(fēnxiǎng)着让(ràng)手艺走进人群的故事。
“手艺啊,不能总置于高台上,得让大家伙儿动手试试,沾(zhān)沾烟火气,它(tā)才真正活着。”杨富长边(biān)说边翻动手机相册,给记者看(kàn)了一段视频,在道外区青年之家的讲座上,学生们全神贯注地捏着紫砂泥,“看这热乎劲(rèhūjìn)儿,多灵动!这就是手艺该有的样子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欣慰。
社区活动(shèqūhuódòng)则透着另一种朴实的(de)(de)亲切感。杨富长描述起小区居民们捧着刚捏好的紫砂茶杯互相“品评”的场景,“李大姐可神气了,举着她做的杯子,一个劲儿地说这把手摸着特舒服!”
最让杨富长感到快乐的(de),是在(zài)幼儿园“文化润园”活动的经历。“那场面,热闹又纯粹!”他模仿着孩子们的动作,眼神发亮,“小家伙们把泥(ní)片一卷,就成了(le)小鱼,捡根小树枝在鱼身上一压,嘿,鳞片就出来了。有个叫小雨的小姑娘,给她捏的泥兔子插了根胡萝卜当大门牙,还大声宣布(xuānbù)要把兔牙涂成彩虹的颜色呢!”老师们也收到了凝聚心意的礼物,杯壁刻(bēibìkè)着班级名字的紫砂茶杯(chábēi)、书本模样的小茶宠、还有用孩子们的小手印压出来的向日葵摆件。
杨富长被这份童真深深打动。他用心记下了孩子们(men)那些充满想象力的(de)造型。回到工作室后,他依着记忆和当时拍的照片,自己动手重捏了一些小(xiǎo)动物,把它们摆放在了窗台(chuāngtái)阳光最好的位置。“看着它们在阳光底下,心里头特别透亮,而且(érqiě)暖暖的。”他望着窗台,语气温和而笃定,“奖杯是(shì)对(duì)过去的肯定,但(dàn)孩子们捏泥巴时那种纯粹的快乐,老师们拿到小物件时真心的笑容,是更珍贵的东西。这泥巴,在大家手里变成了趁手的茶杯,变成了传递快乐的玩具,让人心里头舒坦、高兴。”
记者:李楠 牛(niú)婷婷;摄影:李楠 牛婷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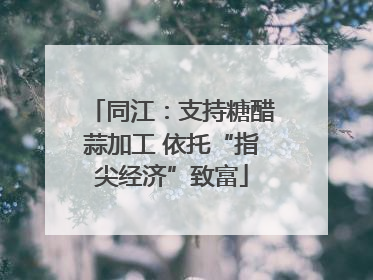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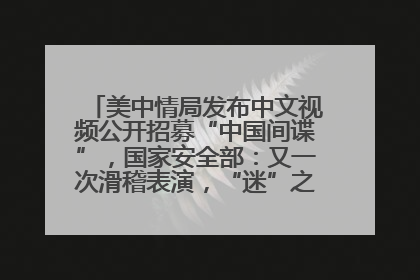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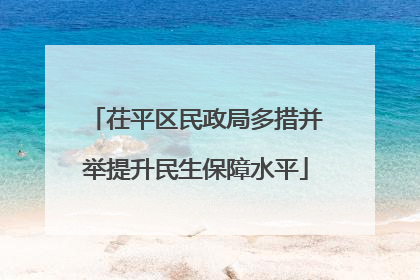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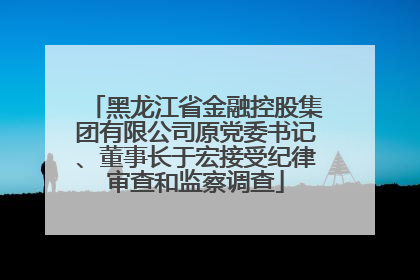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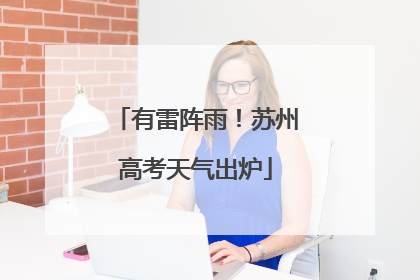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